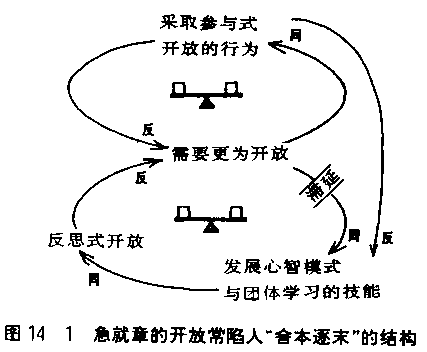隱藏而不易被發覺的舍本逐末結構,總是源自癥狀解逐漸削弱根本解的方式。當我
們愈鼓勵員工說出他們的看法,我們愈可能覺得我們已達到更開放的需要,卻絕對沒想
到我們正逐漸打消了朝向更深層開放的努力。最終結果是產生奇妙的“開放的封閉”
(open closedness)現象,每一個人都覺得他有權發表他的看法,然而卻沒有人真正
在傾聽和反思。相互間漫無目標的談話,取代了真正的溝通與深度匯談。
另一方面,在參與式開放與反思式開放之間也有一項正面的綜效。如果這項綜效建
立起來了,它可成為削弱內部政治化的一股強大力量。依我的經驗,關鍵是一方面使組
織成員在公開表示意見時覺得安全,另一方面是培養成員建設性地挑戰自己和他人思考
的技能。以反思結束政治游戲
現在以一位因“開放”而著稱的公司高級主管的“不幸遭遇”為例,來說明反思式
開放在產生綜效上的關鍵性。這名高級主管發現員工對自己所作的某些決定批評愈來愈
多,但是沒有人向他當面提起對他的看法。在其他管理者的心目中,他只關心表面成績,
對自己所屬單位的關切勝過對公司整體的關切。盡管公司中的人對這名主管的批評甚多,
但員工和其他主管都覺得這只是“個人的”看法,在會議上不適合提起。沒有人當面質
疑他的決定,只是繼續在背后“開放”和坦率地批評他的決定,從未分享對這件事所有
看法背后的想法。
這位高級主管覺得自己慢慢陷入被別人排斥的處境。公司中其他人過去也有過這種
被孤立的痛苦經驗。但對于自己為什么會被孤立,他實在想不通。由于覺得被孤立和攻
擊,他花愈多的時間來說明自己每一個想法,但別人卻反而以為他只關心自己的部門。
實際上,他陷入了一個絕境,無論努力澄清或保持沉默都于事無補,而只會加強別人對
他的負面印象。
為什么其他高級主管(其中有些是他的朋友)不把對他的觀感告訴他?因為他們恐
怕引起不愉快的爭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難以察覺的核心問題,是其他高級主管也
不了解這是怎么形成的;這便是缺乏反思式開放的癥結所在。他們已經斷定自己的心智
模式中對此人的看法是正確的:“只關心表面成績,他對自己所屬單位的關切,勝過對
公司整體的關切,這是一項無庸置疑的事實。”
另一方面,這位被孤立的主管也沒有真正更深入地探究過問題,在會議中,他從不
曾問大家:“等一下我們是不是又陷入一再重復的情勢?”雖然在所有的會議上大家都
聲稱必須要開放,但他覺得那樣問還是不妥。事實上,在每一個共同參與的會議上,雙
方都在玩政治游戲,他玩的是“為自己的決定辯護到底”;而其他人玩的是“老實招出
你真正的意圖吧”。這樣的政治游戲耗損了他們太多的精力,使其他人不可能探討這名
主管任何決定背后的真正理由,或在對他的認知背后真正的推論是什么。換句話說,其
他主管以某些特例的觀察為基礎,作成概括式的論斷,但是他們并未檢驗自己所作的論
斷。其他人在他背后對于這個概括式的看法談得愈多,便愈加深了自己的論斷。這是一
個典型的跳躍式推論。最后,要不是有一位我們的顧問幫助其中幾位主管看清他們自己
的所作所為,這個惡性循環可能一直繼續下去。
他們在一個聚會中跟這位被套人刻板印象的主管坐下來,指出他所說的話,導致他
們對他的觀感:“你使我們覺得你只關心自己部門,而不顧公司整體。”他抗議說他當
然關切公司,至少他心里非常關切公司。是的,他也許有夸耀自己的傾向。是的,他對
于自己有信心的方案會投入大筆的經費。是的,當一個方案受到威脅的時候,他會覺得
有義務站出來為之辯護。但是難道是因為那樣做而使他被認為是整個團隊組織的叛徒嗎?
在那次的聚會中,有些人愿意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情況很奇妙地轉變了。這位高級
主管在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漸漸開始深入了解其他同事關切的本意;而同事們則了
解自己曲解了他的行動。政治游戲開始一步步地堰旗息鼓。這個團體體會到真正的開放
有多么奧妙。他們看到把一位成員套上刻板印象的悲劇性后果,下定決心不再讓這種悲
劇發生。他們學到了單是說出來的開放與真正的開放有何不同。
依我的經驗,當管理者明白反思式開放不僅需要善意,更需要技能,才可能在逆境
中有所突破。譬如,能夠區別由事實直接觀察到的,與基于事實所產生的概括式看法,
將有助于這些主管不致誤將那位高級主管套上刻板印象。在看起來“開放”的團隊組織,跳
躍式的推論尤其危險。當大家自由談論時,意見常能迅速獲得一些共識,因而很快就斷
定所觀察到的是無懈可擊的事實。
開放與系統思考
沒有比“確信”(certainty)更能扼殺開放。一旦我們覺得已有答案,所有質疑
自己想法的動機都消失了。但是系統思考的修煉使我們體認:復雜的問題原來并沒有絕
對正確的答案。就此而言,開放與系統思考是緊密相連的。
有一個名之為“大墻”的簡單活動在我們的領導研習營中使用多年,能夠切中此一
課題之核心。我們以白紙貼滿一面大墻,然后請大家就某項他們正在思考解決的問題,
一起繪出所有的因果回饋關系。譬如有一次,我們請大家運用系統圖來思考怎樣平衡工
作與家庭責任。通常我們開始找出主要變數,交錯地寫在墻上:時間壓力、自己的期望、
責任、個人的興趣、生涯目標、工作地點與住家的距離等等。然后我們開始提出可能的
因果回饋關系:期望會影響生涯目標、上班通勤的時間會影響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個人
所得會影響經濟獨立性和生活預算……。不到一個半小時,我們已經以環路和箭頭畫滿
整片墻壁,在房間內的每一個人都驚訝不已;然而我們也了解,這還只是在真實系統中
許許多多的相互關聯的極小部分。大家漸漸領悟到,沒有人能夠弄清這件事背后所有的
互動關系。
這項領悟對他們有很大的沖擊。有些人給自己借口說:“喔,這太淺顯了,沒有什
么意義。”有些人則問:“這樣的全面思考因果回饋關系的重點為何?”有些人則堅持,
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他們最后一定可以完成它。但是那些真能面對這種“無解”局面的
人,都會笑著坐回椅子上,心中有了更深的體悟。
大墻的啟示
我頭一次看見“大墻”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七十年代后期,系統動力學的前
輩米鐸絲主持的一個三小時的研習會,主題是第三世界營養不良的問題。與會者來自各
國著名的專家,嘗試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從各角度,尋找出全球饑餓的成因模式。沒
多久,在大墻上已經包含許多事情,從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價值到國際貿易。在
旁聽眾中有一位致力于糧食與和平問題的女士,開始嘆氣并搖頭。米鋒絲暫停下來問她
是不是不舒服。這位女士說:“我的天!我總是假設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本以
為政客們知道該做什么事,只是為了政治上的考慮和貪念而拒絕去做。但是現在我明白
沒人知道答案。我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
“大墻”深刻地揭露了一些在我們自己的思考中威權主義的根源。多數人是在權威
的環境中成長的。在兒童時期,父母有答案;在學生時代,老師有答案;進入工作團隊組織
中,上司也必定有答案。人們內心深處已經被灌輸“在上面”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這
種心態使個人和團隊組織的發展潛力受阻,同時它減輕了團隊組織學習的責任。最后當終于明白
“在上面”的人并沒有一切答案時,人們常傾向于以嘲濾的態度面對這些人。
反之,如果團隊組織中的人共同發覺沒有人有答案,它將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使團隊組織
因而掙脫某種束縛。在我們把一大墻”這項練習列入領導研習營以后沒多久,一位波士
頓的高科技公司副總裁,歷歷如繪地描繪出他參加的心境。他研究佛學禪宗已有十年,
是一位很有成就和富于創意的工程師。在做過練習以后,他說:“很多人會說一旦看清
自己永遠無法理解生命后,會否定理性,這是不正確的。只要重新界定理性:追求更深
的理解,但是同時也知道沒有最終答案;這會形成一種創造的過程——它包含理性,但
是還有其它東西。”
無庸置疑的,這便是開放的狀態。如大墻的經驗所證實的,你明白自己的任何“答
案”,充其量不過是“近似值”,總還有改善的余地。你可能不斷在磨練自己解決問題
的理性能力,并在過程中將這項能力盡量發揮,而一直都知道還是不夠。然后,以前被
“我知道正確答案”那種信念所掩埋的好奇心或求知欲,自然浮現出來。“我不知道,
但是或許他知道”,或“我不知道,但是我應當知道”的恐懼開始消除。我們因知道
“我們不知道”,而變得心平氣和,或如愛因斯坦所說的:“我們所能體驗最美的事,
便是無法理解的事,它激發出好奇心,它是所有真正藝術與科學的來源。”
知道答案的錯覺
很不幸的,在當代社會中,知識組成的方式破壞了這種“無法理解”的感受。知識
的分門別類造成在各專業領域中的人一種自信的錯覺。譬如影響管理的傳統學科,諸如
經濟學、會計學、行銷學與心理學,把這個世界明確地區分為許多小部分,每個小部分
配以解答,然后說:“這是問題,而這是問題的解。”但是區分的界限往往是任意劃分
的。就如當有些經營者在思考應將一項重要的問題交給哪個部門來處理時,總是先思考
這是一個經濟問題、會計問題或是人事問題那樣。這個世界原應是整體的,只因我們強
行加上的分析鏡頭,使得問題好像能夠被分隔而得到解決。當我們忘了自己所看到的只
是鏡頭里的東西,我們就失掉開放的精神。
這并不是說所有問題都是無法解決的。有些問題的確有“正確的解”,例如一旦生
產與最終配銷點、需求量與運輸成本確定了,就可以找出設煉油廠的最佳地點;或是一
旦一項新投資計劃選定,而利率與股利比率也確定之后,就能夠決定舉債與股東權益等
籌措資金的最佳組合。處理這類問題時,幾乎可以忽略所有的動態性復雜,而只產生很
小的副作用。不幸的是,這些并不是經營者所遭遇到最重要的問題。
以《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一書聞名的英國經濟學家舒馬克
(E.F.Schumacher),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困惑者指引》(A Guide for the
Perblexed)書中主張,問題有兩種不同類型:收斂性的(conversent)與發散性的
(diversent)。收斂性的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解;愈是理智地研究這類問題,答案的焦
點將愈聚斂而清晰。發散性的問題沒有正確而惟一的解;有‘知識與智慧的人愈是研究
這類問題,會發現并提出愈多互相沖突的答案。發生這樣的情形,問題不在于這些專家,
而是問題本身的性質。舉例而言,假設你在美國,你想從波士頓搭車到紐約州的阿爾班
尼(Albany),最快的是哪一條路線?要找出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并不難;但是“為什
么你想去阿爾班尼?”這個問題則沒有絕對的答案。舒馬克最喜歡的一個典型發散性問
題的例子是:“你認為什么是最有效的教育小孩方式?”隨著不同個性、所處環境和知
識背景,無可避免的,每個人會有相當不同的結論。
必須了解的一點是,發散性問題并非尚未解決的收斂性問題。發散性的問題是沒有
單一最佳解的問題。如舒馬克所說的:“發散性的問題違反一般人心中的思考邏輯——
以逐步、單一的方式解決問題,以消除緊張狀態。”
“培訓人員的最佳方式為何?”“要投資在什么新產品上面?”“使顧客滿意的最
佳方式為何?”這些都是發散性的問題。惟有真正的開放,才可以讓人有建設性地處理
這類問題。
開放的真義
雖然反思與詢問的技能和系統思考的知識,對反思式開放之養成助益頗多,開放卻
不僅是一套技能。如歐白恩所言:“對于涉及人類精神層面的問題,在下處方時,我們
不得不小心翼翼。開放超乎個人的因素,它是一種存在于你和他人之間的關系。它是一
種精神層面和思想狀態的改變,以及一套技能與實踐方法。”
最正確的態度是將開放視為與周遭人或事的關系,而不是一種個人的特質。從某些
角度來看,說“我是一個開放的人”是毫無意義的。同一個人,跟某些人能夠以開放的
心態相處,但是跟其他人則不一定。在這個意義上,就像鮑姆“深度匯談”的概念,當
兩個或更多的人彼此愿意先“懸掛”自己所確信的假設于他人面前,開放的溝通便由此
產生。他們變得樂于分享自己的思考,并且樂于讓自己的思考接受別人的影響。此外,
如鮑拇指出的,在開放的狀態下,他們可以觸及其它方式所無法達到的理解深度。
如果開放是與周遭人或事關系的一種特質,那么建立具有開放特質的關系,就可能
是建立一個具有開放特質團隊組織的最高杠桿點之一。我與我的許多工作伙伴長期反復觀察,
證明確實如此。團隊組織中主要成員之間具有學習效果的關系,對范圍更廣的其他團隊組織成員,
有非比尋常的影響。當一小群人(二或三人)真正地奉獻于愿景及開放時,他們創造了
一個學習型團隊組織的小世界;這個小世界學習型團隊組織并非只教導他們所需要的技能,而且
成了其他人的模范。
追求開放的推動力量,如歐白恩說的:“是愛的精神”。當然愛在企業與管理的環
境上是一個難以使用的字眼。但是歐白恩指的不是那種浪漫的愛。事實上,在開放背后
愛的類型,是希臘人所稱的良師益友之愛(agape),它無關情緒,全然是一種意向:
奉獻于為彼此服務,毫無保留。在開放背后的愛,它的最佳的定義是:彼此全心而無條
件地為另一個人所能夠與希望達成的“自我實現”而奉獻。
歐白恩說:“在追求開放的過程中。如果你只具備渴求的動機,而沒有實踐的技能,
是不會有效果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并未真心想達成開放的境界,而想要培養那
樣的技能,同樣無法充分發揮效果。”
既嚴且慈的良師益友之愛,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愛”的觀念,必須毫不稍怠地去
分享彼此的感受與看法,并且要有開放的心胸接受看法的改變,才能達成。
重新定義“自由”
大多數的人說:“我有自由去做我想要做的,”意思是說:“我有行動的自由,不
必照別人所說的去做,沒有人能妨礙我按自己的意愿行動。”
但是完全沒有外來限制的“自由”,只是像空中樓閣般華而不實。譬如第三章的啤
酒游戲中的各個角色,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決定,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所產生的
結果,幾乎全都與他們原來的意圖相反。因此,盡管他們自由做決定,卻陷入無法控制
的力量中,而有無助的感覺。這是“自由行動”最大的反諷——愈自由反而愈受困于無
助的感覺。這是由于系統結構所產生的束縛。但是,只要他們改變思考與行動的方式,
他們的確有產生較成功結果的力量。
歐白恩說:“在未受外力控制的情形下,人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事實上他
們被一種更深藏不露的束縛所囚禁,那便是他們只以一種方式來看這個世界。”這是由
于心智模式所產生的束縛。
真正的自由絕非擺脫束縛的自由,而是創造我們真正心之所向的自由。那是追求
“自我超越”的人所找尋的自由,那是學習型團隊組織的中心精神;因為開創型學習的動力,
源自想要創造對人們有價值與意義的新事物的欲望。